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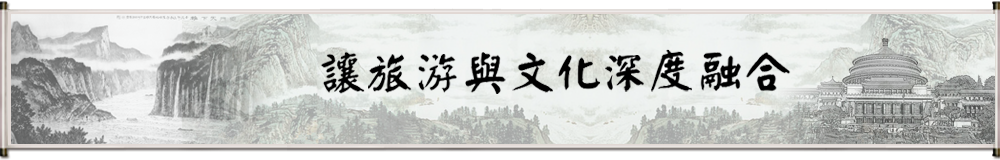
朱熹與長壽的學術淵源
李永明
中國的思想文化,素以儒學為正宗,先后經歷了先秦儒學和宋明理學兩次高潮。先秦儒學,必奉孔子為鼻祖;宋明理學,當尊朱熹為頂峰。蔡尚思先生曾經賦詩贊揚:“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可見,朱熹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地位之顯赫。
長壽,地處巴渝腹心,橫跨長江南北,文明起源甚早,卻并非儒學發達之邦。宋朝以前,已知長壽籍名人只有戰國后期的巴寡婦清,是富甲天下的商業圣母,但并無文化之長。宋朝,長壽的文化突然峰回路轉,相繼誕生了譙定、?淵兩位儒學大師,前者對朱熹理學有孕育之功,后者對朱熹理學有傳承之助,并對長壽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譙定與?淵的籍貫
涪陵北巖書院,自南宋開始即祭祀程頤、尹焞、黃庭堅、譙定、?淵,并修有五賢祠。五賢之中,程頤、尹焞、黃庭堅都是外地謫蜀文化名人,而譙定、?淵則是當地學者。
當今關于譙定、?淵的文章,都說他們是宋代涪州人,或者涪陵人,并注明是今重慶市涪陵區人。這個說法,應該說是有依據的。譙定曾經“自號涪陵居士”;[1]南宋學者王質撰有《涪陵譙先生祠記》。[2]?淵,號蓮蕩,蓮蕩乃宋代涪陵的一個地名,南宋學者度正《權夔憲舉?亞夫遺逸奏狀》稱其為“涪州布衣”。因此,歷代《涪州志》、《涪陵志》,也都記載譙定、?淵為涪州人或者涪陵人。
不過,涪州或稱涪陵,唐宋以來是一直是州名,管轄涪陵、武隆、南川、長壽等縣。譙定、?淵到底是涪州哪個縣的人,一般史書缺乏記載。明朝成化(1465--1487年)《重慶府志·長壽卷》載,譙定、?淵皆為長壽名人。康熙五十三年《長壽縣志》載:“長壽自宋熙寧迄元,歸并涪州,故人物多載涪陵古志。今考名儒如譙定、?淵、賈長卿輩,所居屬境內者方為編入,非因小邑荒陋,借材于楚也。”可見,譙定、?淵,均為長壽人,長壽史籍早有明載。
然而,譙定、?淵到底是長壽哪個地方的人,卻一直不為常人所知,至今謬說流傳。其實,譙定的籍貫,史書上早有明確記載。
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一涪州條載:
皇朝譙定,字天發,樂溫縣玉溪人。深于易,自號涪陵居士。伊川魯直相繼謫居于涪,聞其名,未之識,遂率伊川往訪之,從此深加敬仰。
元人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卷四之譙定條載: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溫縣玉溪人。
樂溫,即長壽的舊名,唐初置,沿用到宋元。玉溪,就是今長壽區西山之外、與重慶渝北區、四川鄰水縣毗鄰的洪湖鎮、萬順鎮地界,長壽習慣上稱大洪湖。
以上二處對于譙定籍貫的記載,當為信史,并可從其它史籍中得到驗證。康熙五十三年《長壽縣志》山川類載:“玉溪,治西七十里,即譙定、?淵二先生講學處”。光緒元年《長壽縣志》載:“縣西七十里?子山下,前臨玉溪,宋儒譙定、?淵講學于此,今有祠。一云,即淵宅故址。”既然,譙定籍貫在玉溪里,?淵舊宅故址也在玉溪里,說明譙定、?淵原來是同出一里的老鄉。明末曹學佺《蜀中廣紀》卷十八載:“玉溪里,在縣西八里,宋賢譙定天發,?淵亞夫所居也。譙學于伊川,?學于考亭。” 此處言玉溪里在縣西八里,有誤。但說玉溪里乃譙定、?淵所居,卻是準確的。
今長壽大洪湖一帶,有眾多遺存,可以看成是譙定、?淵故里的重要證據。
位于長壽區萬順鎮四重村曹家巖組王東庵灣附近的燕子山,即?子山,是譙定、?淵在老家附近的講學之處。光緒元年《長壽縣志》載:“?子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山以宋儒?亞夫得名,地近鄰水界。”光緒元年的長壽治圖,特別標明?子山就在玉溪里。?子山下有個李家大灣,原名?子山下灣,據《長壽?子山李氏族譜》記載,這是長壽李氏祖先之一李濟川明末從湖廣入川后,因仰慕譙定、?淵而選定的李家祖屋。
不久前,?子山出土兩塊已經殘缺的石碑。一塊殘碑保留著“一日至”,“召為崇政”,“窶甚一中”,“山蜀人指”等字樣,這顯然是《宋史·譙定傳》的文字。另一塊石碑上面保留著清晰的“?”字,說明與?淵有關。
在?子山下的王東庵灣,發現了一尊臥牛石雕,雕像憨態十足,栩栩如生,牛背上雕刻著層次分明的蓮花寶座。這尊臥牛石雕,當與譙定有關。譙定曾經寫過一篇牧牛圖詩,共分9章,每章都以牛喻道,反映了譙定的理學宗旨。
明末長壽籍學者李開先撰有《?子山碑記》,文中記述譙定、?淵修身之地有“洗垢池”。[3]在?子山西約一公里山上,有個地方叫金家坪,屬于萬順鎮的白鶴村,這里就是洗垢池的所在地。至今,在一個名叫洗馬大田的水塘石壁上,依然保留著“上古洗垢”四個蒼勁古雅的大字,而周邊地帶就叫“洗垢池”。
二、譙定對朱熹的沾溉
譙定,字天授,一作天發,號達微,自號涪陵居士,人稱涪陵先生,又稱譙夫子,宋代涪州樂溫玉溪人。生活在北宋后期與南宋初期之間,生卒年不可確考。僅從黃山谷謫涪期間專程拜訪而“深加敬仰”看,斷非等閑之輩。
譙定自幼學佛,又從南平(今重慶市南川、綦江一帶)郭曩氏和易學大師邵雍學《易》[4],后往河南師從北宋理學家程頤。宋哲宗紹圣年間(1098—1100年),程頤貶謫涪州,譙定隨師同往,住在涪州長江北岸的北巖研讀《易經》,協助程頤完成了易學研究之集大成著作《周易程氏傳》。宋欽宗靖康初年(1126年),經呂好問推薦,召為崇政殿說書,不就。宋高宗即位,經許翰推薦,高宗詔赴維揚(今江蘇揚州)拜通直郎。因金兵入侵,維揚失守,譙定亦未到職赴任。轉而回到老家研究理學,傳道授業。
譙定的學術,最擅長者是易學。易學,向來分為象數與義理兩派,學者往往擇其一端而修之,很難有象數與義理兼長者。譙定問學于郭曩氏和邵雍,已得象數派的真傳。初學佛典,汲取義理之長,又兩次從游程頤,“獲聞精義,造詣愈至”,又得義理派的妙諦。顯然,在眾多理學家中,譙定是罕見的象數與義理兼長的理學大師。
譙定在當時具有很大學術影響。其嫡傳弟子,著名的有劉勉之、胡憲、張浚、馮時行、張行成等人。再傳弟子中,朱熹、呂祖謙、張栻,人稱東南三賢,分別開創閩學、金華學派和主講岳麓書院,皆為宋代理學大宗師。三傳、四傳、五傳弟子如陸游、王質、?淵、度正、李舜臣、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陽枋、陽岊、高斯德、史蒙卿等,更是遍及全國各地,特別是三傳高足、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開創鶴山學派,為南宋晚期的重要理學學派。《宋元學案》收錄100個學案,譙定門人及其傳承弟子涉及學案多達35個,占三分之一強,涉及學者二百人以上,足見譙定確為一代理學大宗師。難怪,清代學者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稱贊譙定“固程門一大宗也”。
譙定是程朱理學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由于北方淪陷,宋室南渡,理學中心從北方轉到南方,并達到頂峰。而譙定正是宋代理學中心從北方轉向南方,從二程洛學發展到朱子閩學的樞紐人物。
譙定對朱熹的學術影響,主要是通過譙定的兩大弟子,亦即朱熹的兩大恩師胡憲和劉勉之實現的。
清初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曾說:“朱子師有四”。[5]朱熹早年的啟蒙教育,主要是由父親朱松完成的。朱松病逝時,朱熹年甫十四,學業未成,故臨終時諄諄告誡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6]朱松要求朱熹“汝往父事之”的,分別是胡憲、劉勉之、劉子翚(huī)三位大儒。胡憲(1085—1162年),是三位老師中年齡最長者,“熹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為久”。[7]劉勉之(1091—1149年),是朱熹的老師和岳父,史載“熹之得道,自勉之始”。[8]劉子翚(1101—1147年),邃于《周易》,待朱熹如子侄,成為朱熹的義父。
朱熹最后一位老師李侗(1093—1163年),教授朱熹十年,為答朱熹所問,給朱熹寫了24封信,朱熹將之匯集成《延平答問》,對朱熹哲學的成熟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朱熹的四位老師,都傳承程頤、程顥之學,只是傳承的路徑有二:
一條路徑是經劉子翚上承胡安國,經李侗上承羅從彥,再上承程頤、程顥的嫡傳弟子楊時、謝良佐、游酢,按照這個路徑,朱熹為程頤、程顥的四傳弟子。
另外一條路徑,是經胡憲、劉勉之上承程頤嫡傳弟子譙定,按照這個路徑,則朱熹為程頤、程顥的三傳弟子。
第一條路徑,由于程顥曾經對“程門立雪”的楊時有“吾道南矣”的期待,且楊時同時又受教于程頤,因而往往被看作是二程學術的正脈。第二條路徑,由于譙定擅長易學,并協助程頤在涪州完成《周易程氏傳》,而《周易》居六經之首,也是理學的核心,因而被看作朱熹理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源頭。
《宋史·譙定傳》載:“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余意者也”。可見,胡憲、劉勉之,是譙定易學的主要傳承人。
那么,胡憲、劉勉之又是如何學易于譙定的呢?
《宋史·胡憲傳》載:
紹興(當作紹圣)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于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
《宋史·劉勉之傳》則載:
逾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佑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邃《易》學,遂師事之。
這兩段史料,記載了胡憲、劉勉之向譙定學易的時代背景和求學過程。而譙定對兩位弟子也精心指導,使他們最終成為易學的正宗傳人。
程頤曾經講:“易學在蜀”,而譙定正是宋代四川易學的集大成者。這正是胡憲、劉勉之不得不從學譙定,朱熹不得不師法譙定的原因所在。盡管朱熹晚年對譙定的學易方法,頗有微詞,甚至不滿,但并不影響朱熹吸納譙定易學的合理成分。從師承系統上看,朱熹確系譙定的再傳弟子。朱熹易學既重視義理,又吸收象數,就與譙定學風相近,這正是來自譙定易學的影響。朱熹對譙定的另一弟子馮時行十分崇拜,恨不能一見請益;而對馮時行的弟子,四川井研學者李舜臣《易本傳》(佚)有所吸取,從中亦可反映出朱熹與譙定之間的學術淵源。
三、?淵對朱熹的師承
經過兩條路徑的傳承,朱熹全面繼承了程頤、程顥的洛學而發揚光大,最終發展為更具影響力的閩學,成為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在宋代理學發展過程中,四川的蜀學異常活躍,出現了與程朱之學相互融合的趨勢。南渡以后,一些川籍學者,追慕朱熹學術,東出夔峽,不遠萬里,直接師從朱熹,學成之后又將程朱理學帶回四川傳播,?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淵(—1250年),字亞夫,號蓮蕩,南宋涪州樂溫 (今重慶市長壽區)人,是理學大師譙定的同鄉和三傳弟子,更是史學大家李燾(1115-1184年)和理學大師朱熹的嫡傳弟子,是享譽巴蜀的理學家、教育家。
?淵逝世于宋理宗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而其生年沒有明確記載。但從其少年時從李燾游學、中年開始從朱熹游學(1193年)的情況看,?淵至少應該出生于1163年之前,其享年理應在九十歲左右。
?淵平生好《易》,對于“古今易學靡不研究”。[9]?淵“萬里往考亭而師”[10]朱熹,起因是聽說朱熹易學“深得羲、文、周、孔之奧”[11]。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時朱熹始筑室于建陽之考亭,?淵于本年夏天從朱熹游學于閩北建陽三桂里考亭之竹林精舍。朱熹于紹熙四年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曾講學于長沙岳麓書院,?淵也隨同前往,侍學左右,前后“越三年,盡得其說以歸”。[12]?淵與朱熹于宋寧宗慶元元年(ll95年)在長沙分手,直到五年后朱熹逝世,兩人再未曾見面。
?淵是朱熹晚年最為得意的弟子,正如其同門好友度正說:“熹之門人眾矣,惟淵從之為最久,聞其言為最詳,記其說為最備,故其得之為最精。”[13]度正還稱,?淵中年往建寧“從故侍讀朱熹,熹亦愛之,留之門使與諸孫校書”,[14]可見朱熹對?淵是十分喜愛的。
朱熹對?淵的愛重,從朱熹《晦庵集》、《朱子語類》記錄的朱熹與門人的答疑對話中,可以輕而易舉找到很多例證。特別是宋寧宗慶元元年(ll95年) ?淵歸家后,雖然遠隔千里,朱熹仍一如既往地一再過問、指導他的學業,勉勵其讀書問學、進德自愛,關懷之意,期望之情,可謂溢于言表。
朱熹《晦庵集》,至今保留著朱熹晚年寫給?淵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淵回川一年后,托人轉交?淵的,重點是鼓勵?淵修學進德: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亞夫別后,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昻,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于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徳,自愛而已。[15]
第二封信是?淵回川三年后,托門人度正帶給?淵的,既談別后思念之至,也談道德學問修養: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為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徳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為學,所進復如何也。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16]
第三封信是朱熹逝世前一年寫的,除極訴思念之切外,反復強調的依然是修德進學:
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去年度周卿歸,嘗托致意,不知曾相見否。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17]
這三封書信,反映出朱熹對?淵情感之深,寄望之重。以朱熹名滿天下、仰慕者眾的學術地位,對晚輩弟子如此用情殷殷,實在是非常難得,由此可見?淵在朱熹心目中的分量確實非同尋常。
?淵在返回涪陵的當年,就參加了舉試。“適遭權臣以朱熹之學為偽而抑絕之,故雖文理優長而有司不敢取。及朝廷清明,崇尚其學,而淵已衰老,不復從事于科舉矣。” [18]因此,?淵盡管“稟剛健之資,負蓋世之志”,[19]特立獨行,力學不綴,終是一介布衣,老于巖穴。
仕途不通的?淵,學問卻大放異彩。經過長達三十余年堅持不懈的勤學清修,?淵終于“問《易》考亭,得《易》涪鄉,見知聞知,融明寸方”,[20]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易》學思想。而后,?淵出任堂長于涪陵北巖書院,傳道授業二十八載,直至宋理宗淳佑十年(1250年)去世,最終促成了朱熹學說在四川的傳播,即所謂閩學入蜀。此時的北巖書院,依白鹿書院規制而建,學風鼎盛,人才濟濟,與著名的東湖、濂溪、象山等書院并聞于朝野,過往達官顯宦、名流學者無不頻來瞻吊,可謂盛極一時。
?淵的門人,有合州巴川(今重慶市銅梁縣)“二陽”——陽枋、陽岊(jié)。陽枋早年師從朱熹門人度正,后由度正引薦,赴涪陵北巖書院從?淵學《易》,收獲良多。?淵逝世后,又紹師遺德,以古稀高齡主講北巖書院,門人弟子甚眾,人稱大陽先生。枋族侄陽岊,字存瑞,與陽枋為?淵同門弟子,著有《存瑞易說》(今佚),人稱小陽先生。“二陽”易說,下傳宋元之際的理學名家、寧波人史蒙卿,再傳至程端禮、程端學兄弟,發展為浙東理學的靜清學派。
四、宋代儒學對長壽的影響
從朱熹與長壽的學術淵源看,始而因譙定而受惠于長壽,終而因?淵而施惠于長壽,這種學術上的傳承關系,在長壽與朱熹之間建立起了一條特殊的文化紐帶。
朱熹與長壽的學術淵源,還有一個重要例證,那就是長壽定慧寺“天風海濤”的匾額。
定慧寺,位于長壽城區河街之青龍嶺,高聳于長江邊的懸崖上,始建于南宋紹興年間,明朝洪武年間重修牌坊,明末張獻忠入川時遭到毀壞,清朝康熙七年(1667年)重建,至今遺址猶存。長壽的風景名勝,歷來有八景之說。至少從明朝初年開始,長壽八景之中就有“定慧曉鐘”一景,后人有“定慧鳴鐘響萬里”的詩句廣為流傳。
據康熙五十三年《長壽縣志》記載,這“天風海濤”的匾額,乃是考亭朱子的墨跡。考亭朱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由于有朱熹的墨寶,定慧寺歷來是長壽讀書人“習儀朝賀之所”,幾乎成了一個文化圣地。固然,朱熹一生沒有到過長壽,但是,長壽與朱熹卻有著很深的關系,這主要是由朱熹與長壽籍學者譙定、?淵之間的學術淵源決定的。
?淵離世三十余年后,長壽誕生了一位經史學者和文章大家賈元。賈元,字長卿,號易巖,重慶府涪州樂昌縣(今重慶市長壽區)人,是元朝巴蜀地區最有影響的經史學者和文章大家。生活時代大約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三年(1283—1363年)。
賈元因經史淹貫,文章稱雄,素為人所敬慕,然不入仕宦,清貧高雅,終于布衣。最早記載賈元事跡的是明朝楊慎(升庵)的《蜀中人物記》:
賈長卿,名元,號易巖。淹貫經史,以文章名。凡使蜀還者,士大夫相訪,必首問:得賈長卿文字否?其為人所敬慕如此。
楊慎在《全蜀藝文志》中還明確記載,賈元“號易巖,長壽人。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其取字號以此”。后來的《蜀中廣記》、《四川通志》、《同治重修涪州志》、《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康熙《長壽縣志》等書,均明確記載賈元為長壽人。
淹貫經史,是賈元的學術功底;以文章名,是賈元的最大成就。難怪當朝權貴凡是使蜀還京,士大夫相訪必首問“得賈長卿文字否”,可見他的文名早已震動京城,人們無不把他的文章視為珍寶。
賈元留傳至今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涪陵學宮碑亭記》,也稱《文廟御碑亭記》,至正十三年(1353年)涪陵文廟新建碑亭落成時,奉郡守僧嘉閭之命而作。另外一篇《涂山古碑記》,至正十五年(1355年)費著任重慶路總管時,涂山禹廟重修,賈元受費著之請而作。文章針對“禹娶涂山”之說“涂山”究竟何在的爭議,得出巴郡涂山為禹娶涂山氏之所的結論,考證精詳,論據充分,頗具說服力。此文堪稱有元一代的文章精品,歷來受到文選家重視,已經收入近年出版的《重慶讀本》。
賈元還是名重當時的書法家,書學蘇(軾)體,溫雅有法,名盛一時。涪陵北巖“觀瀾閣”(取自朱熹詩句“每向狂瀾觀不足”)匾額和《文廟御碑亭記》,是其遺墨,筆法蒼古,韶秀俊逸。
賈元有個得意門生,名叫冉聰,是長壽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進士,也是有元一代長壽唯一的進士。以文學稱,元至正六年(1346年)撰有《金盤山龍洞記》,著錄于歷代《長壽縣志》。
明清兩朝,長壽舉業發達,人才輩出,成為文化發達的重要標志。據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記載,明清540余年間,長壽文科進士總共52名,占全國文科進士總數51444人的1.01‰,平均每10.46年就出一位進士。其中明朝進士在當時的四川省115個州縣衛中排名第十,在重慶21個州縣衛中排名第四,在渝東地區州縣衛中排名第一。清朝進士在當時的四川省排名第七,在重慶排名第三,在渝東地區排名第二,先后誕生了張蘭清(雍正)、韓鼎晉(乾隆)、李莒(嘉慶)、汪敘疇(同治)、華宗智(光緒)五個翰林。不僅如此,一些文化家族開始嶄露頭角,成為科考大戶。在明清兩朝的長壽進士中,李姓進士達11人,占總數的五分之一強,遠遠多于他姓。有的家庭兄弟皆中進士,如嘉慶道光年間的李郁然、李彬然兄弟,同治年間的汪敘疇、汪范疇兄弟。
這些長壽走出的進士,有的在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跡。聶賢,是明朝三朝元老,歷任工部、刑部、戶部三部尚書。李彬然,曾任道光年間成都錦江書院、重慶東川書院山長。汪敘疇最有影響的事情,是主持慈禧太后40壽辰慶典和60壽辰慶典。李滋然,著名經學家,又是康有為、梁啟超的恩師。張賓吾,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四川文史館館長。
宋代以來的文化崛起與傳承發展,對近現代長壽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清末廢除科舉后,長壽新式教育蓬勃發展。1905年,鳳山書院廢止,林莊學堂創辦。知縣唐我圻親筆題寫楹聯:“世方求異等茂才,為吾道任干城,豈圖柔史剛經,多能鄙事;我自愧不學無術,與諸生開石室,應有干家棟國,共濟時艱。”并題贈“百年樹人”的橫匾。此后,林莊學堂作為長壽地區的最高學府,成為長壽教育的一面旗幟,并見證了近現代長壽的歷史。1911年11月18日該校教師廖樹勛帶領學生武裝起義,建立了辛亥革命后重慶第一個獨立政權,這一天也成為重慶獨立紀念日。1925年8月,李一鄂以林莊學堂為據點,秘密成立中共長壽(臨時)黨組織(有稱臨時黨支部),成為重慶市最早的中共黨組織。
各種優秀人才在近當代的集中涌現,是長壽歷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重要標志。李壽民,即還珠樓主,是近代著名的武俠小說大宗師和京劇劇作家,是中國現代罕見的高產作家,也是重慶作品數量最多的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大影響。陳銘德,著名報業家,新民報系的創始人。楊公托,著名美術教育家,重慶美術專科學校創始人。傅潤華家族(傅志清、傅天正、傅起鳳、徐秋、傅騰龍、傅琰東等),是中國現當代最大的魔術藝術家族。雷平,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其在《抓壯丁》中的三嫂子形象,受到觀眾好評。雷雨聲,著名音樂家,《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歌》作曲者。孫經信,著名歌唱家,音樂芭蕾舞劇《白毛女》的首唱。彭光欽,一級教授,著名植物學家,被譽為中國橡膠之父。孫仲山,近代著名實業家、金融家,大中銀行的創立者。雷堯階,長壽沙田柚之父,對長壽沙田柚產業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
總之,譙定、?淵的誕生及其成就在儒學史上的重大影響,特別是他們與朱熹理學之間的淵源關系,標志著長壽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到來。從此,作為蜀中名縣,長壽文風日熾,人才輩出,開始在中國文化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3年10月26日
參考文獻:
[1] 祝穆,《方輿勝覽》[M]卷61涪州,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王質,《雪山集》[M]卷7,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M],重慶圖書館藏本。
[4] 《宋史》[M]卷387,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M]卷39,中華書局,1996.12。
[6] 朱熹,《晦庵集》[M]卷90,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8] 《宋史》[M]卷459,清文淵四庫全書閣本。
[9] [10] [11] [12][19]陽枋,《字溪集》[M]卷8,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14][18]度正,《性善堂稿》[M]卷5,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16][17] 朱熹,《晦庵集》[M]卷63,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陽枋,《字溪集》[M]卷9,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朱熹與長壽的學術淵源》內容提要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朱熹與長壽的學術淵源,從而對宋代以來長壽的文化發展歷程,做出輪廓式描述。朱熹是繼孔孟之后,中國最有影響的儒學領袖。長壽位居西南,儒學起步較晚,直到兩宋之際開始,譙定、?淵等儒學大師相繼出現,才終于迎來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譙定是象數與義理兼長的易學大師,是宋代理學從二程洛學到朱熹閩學的關鍵人物,對程朱理學的最后形成有重大繼承傳播之功。?淵是朱熹晚年的高足,在朱門眾多弟子中從游最久、聞言最詳、記述最備、得之最精,晚年主講涪州北巖書院,成為理學涪州學派的中堅。本文認為,以朱熹與長壽學者學術互動為特征的長壽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極大地促進了長壽儒學的發展,對長壽在元明清乃至近現代的文化發展產生了長久影響。
(作者李永明,重慶航美咨詢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通訊地址:重慶市渝州路132號7棟8—4號;聯系方式:13983165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