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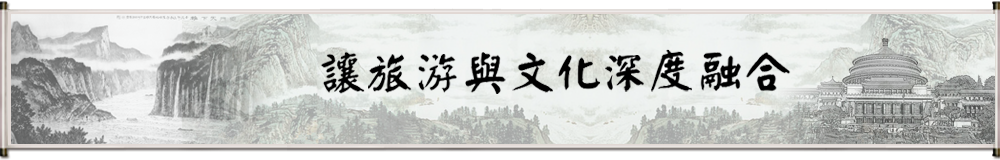
說起定慧寺的青龍閣,一般人已經不知其然。但是,對于年長的長壽人來說,青龍閣卻是他們美好記憶中的一個點。
青龍閣影依舊在
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有這樣一段記載:
青龍閣,邑南五里,瀕臨大江,與白虎頭相對峙。清末邑人孫仲山捐資千元創建。旁有小閣,風景優美。閣內題聯甚多。
青龍閣,位于青龍嘴的懸崖邊,視野異常開闊,懸崖之下是著名的小巖子碼頭和波濤滾滾的長江,北望陡巖重崗的白虎山,亭閣典雅,花木掩映,江天一覽,景色俱佳。
青龍閣的準確位置,好多人已經不太清楚。遠遠望去,定慧寺旁邊有一棟體量高大的蘇式建筑,聳立于青龍嘴上,顯得特別搶眼。一些人誤傳,說這棟樓就是當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及獅子灘電廠辦公大樓。事實上,這棟大樓是1956年7月獅子灘電廠廠部搬遷到鄰封上硐后,原獅子灘水電工程局與獅子灘電廠交換場地而為安置獅子灘水電工程局的家屬才新建的職工宿舍。這棟大樓,與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及獅子灘電廠,沒有任何關系。
青龍閣的面積,大約有50來平方米,四周是花木扶疏的小園林,與定慧寺緊緊相連,相映成趣,過去是長壽民眾觀江游覽之所。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為青龍閣的消失而惋惜遺憾。其實,青龍閣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被另外一個建筑物遮蔽起來了。這棟職工宿舍大樓,就是青龍閣的所在地。原來,這棟大樓就是在青龍閣基礎上,四周增加了框架,上面增加了屋頂,于是外形大變,而把青龍閣包裹在里面了。現在走進這棟大樓,就會發現青龍閣的巨大磚砌圓形房柱,還原封不動地保存著。只要將后來增加的框架和屋頂拆除,青龍閣就可恢復當年的光景。
青龍閣與定慧寺之間,有一棟兩層的樓閣,前后有兩個石朝門。第二個石朝門之前,是一坡石梯,登山石梯,就到了青龍閣,遠處看小樓閣與青龍閣渾然一體,其實是兩個建筑。這個樓閣,就是《長壽縣志》記載的青龍閣“旁有小閣”的樓閣了。
奇靈氣脈沖龍閣
青龍閣四檐高翹,翼然若飛,點綴于青龍嘴上,為定慧曉鐘增添了靈性,儼然成為江上一景,極得江山之勝,因而“閣內題聯甚多”。不過,眾多的楹聯已經無從欣賞,有幸的是,長壽知縣趙維城的楹聯卻得以流傳至今,從中可見當年青龍閣的小景勝概。
對于趙維城,一般人已經沒有什么印象,但他卻是長壽有史以來少有的好官。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卷五,有這樣一段記載:
趙維城,字蕓蓀,江蘇長洲人,優貢,儉樸廉勤,不煩不擾。時煙禁綦嚴,下鄉督鏟煙苗,山民抗拒,幾釀事變。蕓蓀愷切勤諭,卒至禁絕。若非反正后駐軍保種,希圖借此籌款以飽私囊,計此毒卉已無一莖矣。未幾,調署大寧豐都。民國元年,復知縣事。士民愛戴有加,于鳳嶺街鑿池蓄水,石壁鐫“盟心白水”四字,至今人稱趙公井云。去任后,邑人復于平地樓臺,設長生祿位,與霍公雨霖并祀。宣統元年任。
可見,趙維城是江蘇蘇州人氏,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和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兩度主政長壽,“以城苦飲水,鑿池蓄水,以供民飲用”而人稱趙公井,故而極受愛戴,在長壽歷史上實屬罕見。
趙維城的青龍閣楹聯是這樣的:
名士五百年,奇靈氣脈沖龍閣;
春光二三月,罨畫江山接鳳城。
這副楹聯,看似簡單,卻并不好解。其實,趙維城的楹聯,也許是受到其老家江蘇南京莫愁湖畔勝棋樓的影響。勝棋樓始建于明洪武初年,相傳是明太祖朱元璋與大將徐達弈棋的地方。清末著名湘軍將領、湘軍水師創建者、中國近代海軍奠基人彭玉麟(1816年-1890年),在任兩江總督期間,曾經為勝棋樓寫下了這樣一副楹聯:“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聯氣;春光二三月,鶯花合是美人魂。”
兩相比較,趙維城寫青龍閣的楹聯,顯然受了彭玉麟的啟發。名士五百年,是相信長壽一定會孕育出英雄豪杰。這句話,是孟子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的濃縮。奇靈氣脈沖龍閣,是贊美長壽的雄奇靈異之氣,全都集中于青龍閣上。春光二三月,是說青龍閣的風景,以二三月的春光為最佳。罨畫江山接鳳城,是贊美長壽江山如畫,覆蓋了整座城市。罨(yǎn)畫,本指色彩鮮明的繪畫,多用于形容自然景觀或建筑物的艷麗多姿。上聯言龍閣,下聯言鳳城,顯然有祝福長壽龍鳳呈祥的雅意。
青龍閣建成后,成為眾多文人登臨寄興、寫詩抒情之地。其中,目前僅存的是這首《登青龍閣》:
無限韶光好,黃鳥轉枝頭。
驚起山中客,來登江上樓。
云陰宿窗隙,林影落春流。
笑指仙源路,從茲覓小舟。
關于這首詩的作者,民國十七年《長壽縣志》記述為鐘文鼎作,而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則記述為李光蟠作,當以李光蟠為妥。李光蟠,字根仙,清末民初長壽人。是李開先的十世孫,又是還珠樓主李壽民的堂伯。
全詩極贊青龍閣風光之優美,足以引發人歸隱桃源的佳趣。其中“云陰宿窗隙,林影落春流”一聯,頗得山水神韻之勝。
俠商孫仲山
在長壽城鄉,只要提起孫仲山,年長的人幾乎無人不知,且眾口一詞:孫仲山是大富豪,做了很多善事。
其實,從長壽走出的孫仲山,是俠客中的富商,富商中的俠客,其人生充滿傳奇故事,令人肅然起敬。
1936年5月24日,孫仲山在北京度過六十大壽,親朋故舊,賀壽者眾。在眾多壽匾和壽聯的署名中,赫然寫著段祺瑞、吳佩孚、班禪厄爾德尼等社會名流的大名,讓人感到驚訝不已。
而孫仲山的交往圈,更是給人以強烈震撼。孫仲山的交往人群中,有這樣一批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光緒、載灃、載振、那桐、惲毓鼎、袁世凱、黎元洪、端方、盛宣懷、程德全、松壽、陸宗輿、鈕承善、張作霖、張瀾、汪云松、劉湘、楊森……。
原來,孫仲山,斷非人們津津樂道的等閑富紳,乃是清末民初有影響的政治人物,更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實業家,金融家,理財家,公益慈善家,社會活動家。在近代長壽眾多歷史名人中,論經歷之坎坷,創業之艱辛,資財之雄富,交際之廣泛,角色之多元,貢獻之特出,影響之深廣,恐怕無人可與孫仲山相伯仲。
孫仲山(公元1877—1950年),又名鴻猷,長壽縣千佛鄉(今重慶市長壽區江南街道)孫家灣人。
早年在重慶永興隆字號作學徒,后去天津鈞記大米莊,為洋商代銷面粉,從中賺得白銀30余萬兩,一舉成為巨商富戶。孫仲山將賺得的白銀10萬兩匯回家中,廣置田地和修房建屋,大興土木。將剩下的白銀繼續經商辦實業界。同時,還在北京、福建、江蘇、安徽、四川等地政界、商界謀官任職,從中又集聚了大量錢財。
孫仲山任職于政、商兩界,從中結識了四川大中銀行股東汪云松、何鼎臣二人。汪、何二人對孫仲山的為人行事倍加賞識,極為器重,便全權委托他在京籌備北京分行。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孫仲山于1919年在北京前門外大馬神廟,辦起了“四川大中銀行北京分行”,資金總額100萬元,報經財政部注冊登記營業。孫仲山出任分行總經理,從此躋身金融界。
躋身金融界的孫仲山,幾經奮力拼搏,廣結社會各界,實力日漸豐盛。1928年,他在奉系軍閥閻廷瑞、吉林督軍孟恩遠、河南幫同和裕大銀號部經理王安卿、前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河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等政、軍、商界要員、巨商的支持下,投資總額千余萬元,在天津開辦了大中銀行,并對外發行鈔票,為財政部推銷公債,還給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張弧打折銷售部分印花稅票等,從中獲取了大量利潤。繼后,孫仲山又在哈爾濱、濟南、開封、上海、漢口、長沙、徐州等大中城市設立了分行。為了廣結盟友,防御風險,孫仲山還邀請了王懷夫之子王錫恒、馮國璋之子馮季遠入行,對金融干員常鑄九委以重任等。使孫仲山開辦的大中銀行,在各種金融風險中,都能抵御風險,化險為夷。
抗日戰爭爆發后,天津、哈爾濱、濟南等地相繼淪陷,孫仲山的大中銀行經營發生困難。為了保住資產不受損害,孫仲山除繼續從事金融業務外,還廣開財路,兼營汽車、棉布、顏料、絲織品、工業鉆石、稀有金屬等,賺取利潤。
1946年,天津國民黨中央銀行以產業處理局的通知,對孫仲山經營的京、津大中銀行進行查封。孫仲山深感處境不妙,便與上海交通銀行董事長趙棣華合作,接辦大中銀行,更名為“大中商業銀行”。不久,孫仲山回重慶接辦了怡豐銀行,并任董事長。
新中國建立后,孫仲山接受政府關于停業清理的決定,并親自督辦京、津、滬、渝各銀行的清理工作。可惜在清理工作接近尾聲時,孫仲山因心臟病發而不幸辭世。
守孝不忘桑梓
也許人們想象不到,孫仲山捐資1000元大洋修建青龍閣,正值父親逝世本人回鄉守孝期間。
1908年,棄商從政的孫仲山,已經官居二品道員。閩浙總督松壽認為孫仲山才堪大用,入奏朝廷,以備錄用。軍機處隨即做出重用的安排,準備“遇缺即放”。
正當孫仲山宦海得意之時,父親孫繼寬逝世。清制,內外文職現任官員,遇親生父母病故,從聞訃之日始,必須離任守制(守孝)兩年又三個月,稱為丁憂。于是,孫仲山奔喪回籍,在江南老家守孝,這是孫仲山離開長壽后回家居住時間最久的一次。
孫仲山把父親的葬禮辦得轟轟烈烈,影響很大。清政府給孫濟寬追贈了“榮祿大夫”的封號,這是一品散官的頭銜,足見清廷對孫濟寬的看重。孫仲山把父親的墓園,選在江南千佛場的九洞橋,陵墓規模宏大,氣勢非凡,構筑考究,花費不菲。墓成,由四川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被譽為四川歷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維新運動倡導者宋育仁(公元1857-1931年)撰寫碑銘:“惟義方之教,貽親以令名。起布衣以有聞,垂千祀兮清芬。”這個碑銘,對孫濟寬的教子有方,對孫仲山的政商令名,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孫仲山在守孝“居禮之余,捐資十余萬金,補助重慶商業學校,創辦長壽男女學校暨義倉、醫院、公園等處,修筑道路、橋梁、義渡、善堂及救生船等項,冬令施棉衣設粥廠。”
當時,“十余萬金”是一個很大的額度。所謂“金”,絕非黃金,而是白銀“兩”的雅稱。十余萬金,就是白銀十馀萬兩。
捐資辦學,是孫仲山這次資助的重點。重慶商業學校,屬于實業學堂,孫仲山對其捐資補助,與其素重實業的情懷和實業救國的主張,顯然有直接關系。孫仲山資助的長壽男校,當是長壽中學的前身,即位于林莊壩的長壽縣高等小學堂。長壽女校,是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長壽知縣唐我圻花六百金購買城內林莊口的韓侍郎(清代翰林韓鼎晉)花廳另辟校門而興辦,興辦之初,經費相當短缺,堂長不支薪水,孫仲山的捐助,可謂解了燃眉之急。
注重民生,是孫仲山資助長壽的一大特色。創辦義倉、義渡、善堂、粥廠、醫院、公園,修筑道路、橋梁、救生船等,無一不是事關民生的項目,而且著力點全是處于社會下層的普通民眾。
孫仲山捐資興辦公園,指的就是青龍閣。為了豐富定慧寺的景觀,為長壽父老鄉親提供一個休憩娛樂的場所,孫仲山慷慨捐資,特意在青龍嶺上建起青龍閣。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青龍閣建成開放,受到當地官員和民眾的歡迎,因而才有“閣內題聯甚多”的盛況。
孫仲山的佛緣
孫仲山在定慧寺捐資修建青龍閣,除了桑梓之情、慈善之懷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孫仲山對佛學的虔誠信仰。
孫仲山是佛教信徒。孫仲山的老家長壽江南千佛鄉,是一個佛教氛圍很濃的地方。成年后漂泊在外的孫仲山,始終與佛結緣,受佛教慈悲博愛的思想影響至深。供佛堂,掛佛珠,念佛經,印佛書,交僧侶,已經成為孫仲山生活中不可功缺的一部分。
特別是捐助善款,支持佛教事業,更成為孫仲山佛教信仰的特殊體現方式。
北京有兩處佛教圣地——白衣庵和臥佛寺,是著名的文物古跡。
白衣庵位于東城安定門內方家胡同路北,據專家考證是明朝時候的建筑,這座京城最大的尼廟在歷史上有過輝煌,清乾隆時木刻版的京師全圖,民國初年的北京內外城詳圖中,均有白衣庵位置的標注文字。至今,白衣庵還保留著四層殿宇和跨院的古老建筑風貌。
臥佛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區西山馀脈聚寶山(又名壽安山)南麓,背倚山巖,前臨田野,離北京主城約20公里。臥佛寺始建于唐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以后各代有廢有建,寺名亦隨朝代變易有所更改。由于唐代寺里就有檀木雕成的臥佛,元至順元年到至順十二年間(公元1330—1341年)又鑄造了一尊釋迦牟尼大型涅盤銅像,因此,一般人都把這座寺院叫作“臥佛寺”。明宣德、正統年間,朝廷曾經頒大藏經一部置諸佛殿。寺的建筑是一個大院落,在一條縱軸線上排列著四座殿堂。現存寺廟建筑,多是清代重修后的規模。
民國初期,白衣庵和臥佛寺由于年久失修,殘破不堪,一片冷清。為了保護文化遺產,孫仲山帶頭捐資,并發動志同道合者捐贈,先后對兩處佛教遺跡進行修復。白衣庵和臥佛寺,目前已經面貌一新,朝拜者眾,其中應該說也有孫仲山的一份貢獻。
資助印刷出版經卷善書,是孫仲山在佛教事業上的一大功德。《梵網經菩薩戒》,亦名《梵網經菩薩戒本》,或《大梵網經菩薩戒本》,是記述釋迦牟尼弘揚佛法的重要經典。此書于將近一千六百年前,由鳩摩羅什(公元334—413年)大師節選翻譯,并依之為一批弟子授戒,當是華夏傳授菩薩戒之始。然該“戒本”譯于大師晚年,尚未推敲潤色,鳩摩羅什便溘然駕鶴歸西,致令譯本留有缺憾,一些地方生疏隔膜,義理難明,令人費解。于是,歷代注釋本經的著作層出不窮,其中一本是唐朝時候新羅高僧義寂編著的《梵網經菩薩戒本疏》,重點對《梵網經菩薩戒本》中的戒律條目做出注釋。這部佛經中國早已不傳,而保存于日本江戶幕府寬政五年(1793)收錄的臨濟宗大典《送書目錄》中,孫仲山輾轉獲得此書,奉為至愛。民國十一年(公元1922年)一月,孫仲山將此書捐贈出來,交由北京刻經處刻印,從此這部佛教經典才廣為流傳。
1950年5月7日,孫仲山逝世于天津。后來,因為城市建設需要,安葬孫仲山的浙江義地墳墓外遷,孫仲山的遺骸從此不知所終。而今,位于北京西山的佛山陵園,終于有了孫仲山的陵墓,從此,孫仲山安歇于青山綠水,與佛永伴。
有虔誠膜拜的佛教信仰,有自利利他的佛教精神,有樂善好施的仁慈胸懷,有報效桑梓的純樸情感,這,也許就是孫仲山捐資修建青龍閣的因緣。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